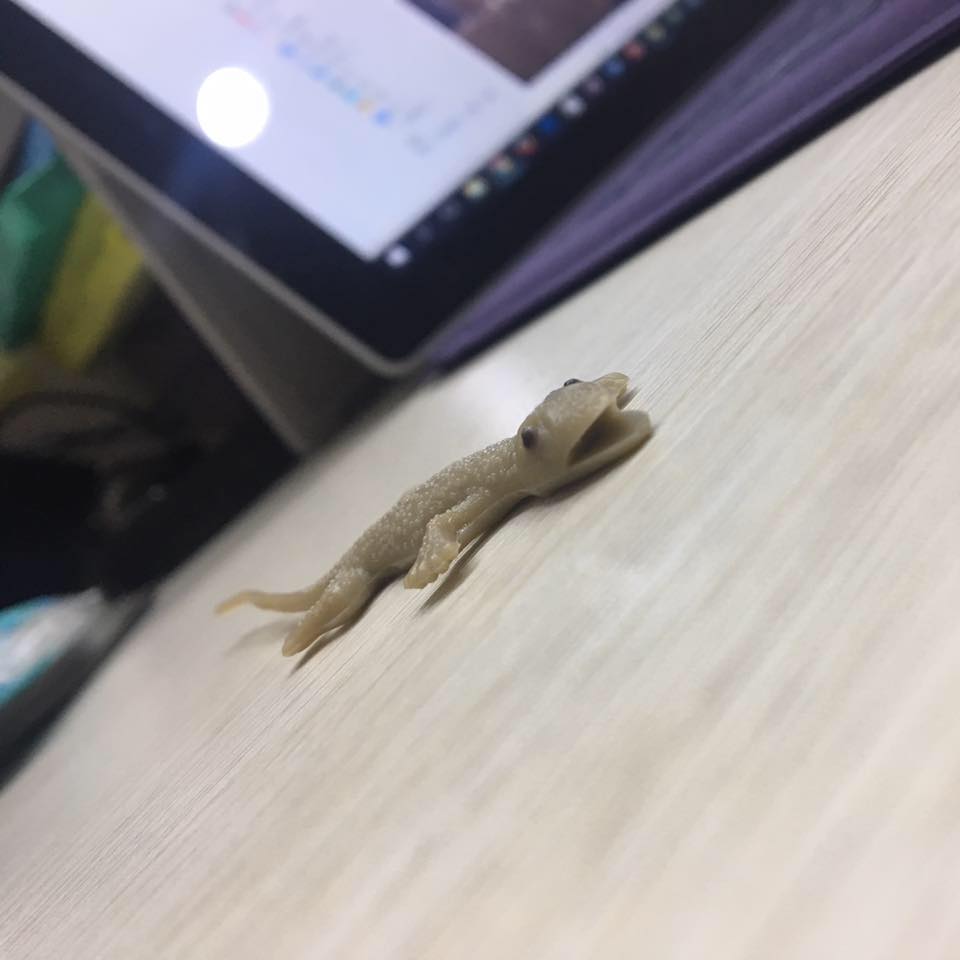文/壁虎先生
原文刊載於《The Affairs 週刊編集》第四十五期(2021.04出刊)
2018年,一個居住在莫斯科的天才獨立遊戲製作人yeo,以模仿8-bit像素化復古風格的遊戲《石河倫吾的朋友們》(The friends of Ringo Ishikawa)騰空出世。這個關於一個日本叛逆高中生和他的死黨們畢業之前最後一個秋天的遊戲,彷彿是《熱血系列》(Kunio-kun)的當代化,卻是以一種逆反的姿態,透過引入「不斷流逝的時間」與「去目標化」,將一種無法消解的存有之憂傷帶入這個理當陳舊的類型故事中。遊戲中大部分的「時間」,除了幾段關鍵的劇情,我們不被強迫完成任何的「目標」(objective),遊戲甚至不會教你怎麼玩它。你可以去學校上課、在屋頂和同學對話、在街上跟不同校服顏色的NPC打架、去健身房鍛鍊,或者全然地錯過全部,而只是在街上晃蕩。你可以在夜晚的公園長蹬上抽菸,你也可以不進食,但你永遠不會「餓死」;你可以只是在臥室裡打電動或就只是「無所事事」,而時間在你眼前流去。大部分的段落,遊戲的推進機制被「去目標化」,成為時間流逝本身。而你也可以去書店買一本書然後「閱讀」它,例如FD的《Brother》——調皮地暗示是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等,但你不會真的「讀到它」。你只是按下一個鍵,然後看到石河倫吾拿起書的專注動作和標記頁數的數字在奔跑,然後數字跑完,看到他發出的一句評語。按住按鍵的時間就是你的「閱讀」時間,儘管我們並沒有真的「閱讀」到任何東西。因此儘管我們依然能滿足於各種目標的達成,但時間的開放性、無目的性和無可抵擋的流逝,導致它持續地關於某種不確定性,並將玩家拋入其中。這也是為什麼當遊戲結尾,當開頭那群與石河倫吾一同在公園與敵黨械鬥的朋友們紛紛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走向不同的生命道路,只剩下石河倫吾一個人在雨中的月台赴約,擊倒一批又一批的敵人,我們不免要意識到一紀重拳向玩家擊來:「啊!我就要消失了呢!」宛如《銀翼殺手》(Blade Runner)最後羅伊的台詞,黑幕漸漸淡入,石和吾倫因為像素化而無法解讀的面容在我們眼前、在雨中消失,像是雨中的眼淚。
尚‧皮耶‧梅爾維爾、吳宇森和路易·馬盧
2020年yeo推出了第二個8-bit風格遊戲《逮捕石佛》(Arrest of a stone Buddha)並以更極端與極簡的方式在遊戲中進行他對「時延」(duration)的實驗。這個更加抑鬱,關於一個1976年巴黎殺手的遊戲,被切割成兩個互不侵犯的塊狀部分,並交替輪環:橫向轉場/卷軸的超高密度射擊;在巴黎街頭漫無目的地遊蕩。
在前者中,你必須自行發現幾個規則:你彈無虛發槍槍致命,但敵人數量荒謬並同時從你的前方和後方像潮水般奔向你,而你不能裝填彈藥,只能從奔來的敵人手中「奪槍」。甚至你只能「低速步行」,只能承受幾發子彈,而除非抵達一個「轉場點」,敵人會無限增生(spawn)。因此你「必須」在每一個敵人出現並開槍前向前輾壓推進,並同時重複「轉身」射擊,強度接近歇斯底里;在後者中,你在與接頭人的短暫交談後便被拋進冷調的巴黎街頭,你徹底地「沒有目的」,在一個只有一間藥局(賣安眠藥)、一間電影院、一家酒吧(賣菸,抽完了必須再去買)、一家服飾店、一個你自己的公寓、一個什麼都沒有的電梯大樓樓頂和一間美術館的街區,你唯一的目的就是「閒晃」,但不論你做什麼,或什麼都不做,時間都會「過去」,並日夜循環,直到下一場「暗殺」。安眠藥能加速一個夜晚的經過,但大多時日你不能購買,一定時間前也不能吞食。除了每次完成任務後和你短暫對話的接頭人,在遊蕩的巴黎,除了最低限度買賣行為,沒有任何一個實質意義上能夠「互動」的NPC,也沒有任何「可積累之物」。所有人都與你無關,他們宛如鬼影。只有你,和時間。
直到不知道第幾個晝夜,當Erik Satie的《玄秘曲1號》(Gnossiennes No.1)出現時我才首先意識到這是什麼:這是路易·馬盧(Louis Malle)的《鬼火》(Le Feu follet)。我們宛如片中的Alain,剛從戒斷(癲狂)中出院,卻依然與世界意義孤絕。《鬼火》中的同一首曲子出現在這裡,召喚著同一個靈魂,而他也有一個愛人。遊戲中一個街邊的門,進去會淡入一個(疑似)女人的房間,但每次進去(如果得以進去),我們只會看到主人翁坐在床邊,而床上「疑似是」一個轉過頭去的睡姿女人,或是什麼也沒有?因為像素太低我們無從辨認。我曾在那裏待了一整個遊戲時間的晝夜,但除了窗外變化的雲彩,什麼也沒有發生,除了夜晚。
這同時是一個尚‧皮耶‧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的世界,它屬於《午後七點零七分》(Le Samouraï)中的那同一個巴黎,而遊戲就發生在這個梅爾維爾式簡潔、沉默、苦修世界之中,配樂不時宛如獸鳴的低頻震盪,呼應著這頭沉默的老虎。最後是吳宇森(John Woo),射擊段落子彈與敵人荒謬的數量和強度,和悲劇英雄式配樂中音符爬升的顆粒分明,無處不是吳宇森式的狂喜(ecstasy)。或許也是因此,遊戲中你唯一能「擁有」的物件,是周潤發那身風衣和墨鏡,而我們可以像《喋血雙雄》(The Killer)中的小莊搭上遊艇瀟灑逃逸,即便這份瀟灑是如此地短暫。我非常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英雄本色》(A Better Tomorrow)和《喋血雙雄》正是誕生自吳宇森對梅爾維爾和當年存在主義浪潮崇敬地臨摹。
在遊戲中有一家電影院,你可以進去「看電影」,但因為影廳被展現為一個側剖面,我們不會真正看到銀幕,宛如《石》中的「讀書」,我們因而只會看到打在銀幕和觀眾席間的光線,和同樣無法解讀的主人翁的臉,我們進去,只是為了「消磨時間」。只是透過配樂,我們知道什麼人或許正在心碎?這三位導演的電影疊映在《逮捕石佛》中因而不是一個巧合,這只是yeo在創作中進行美學系譜「翻土」的結果,而在遊戲感謝名單中,這三位導演被直接點名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