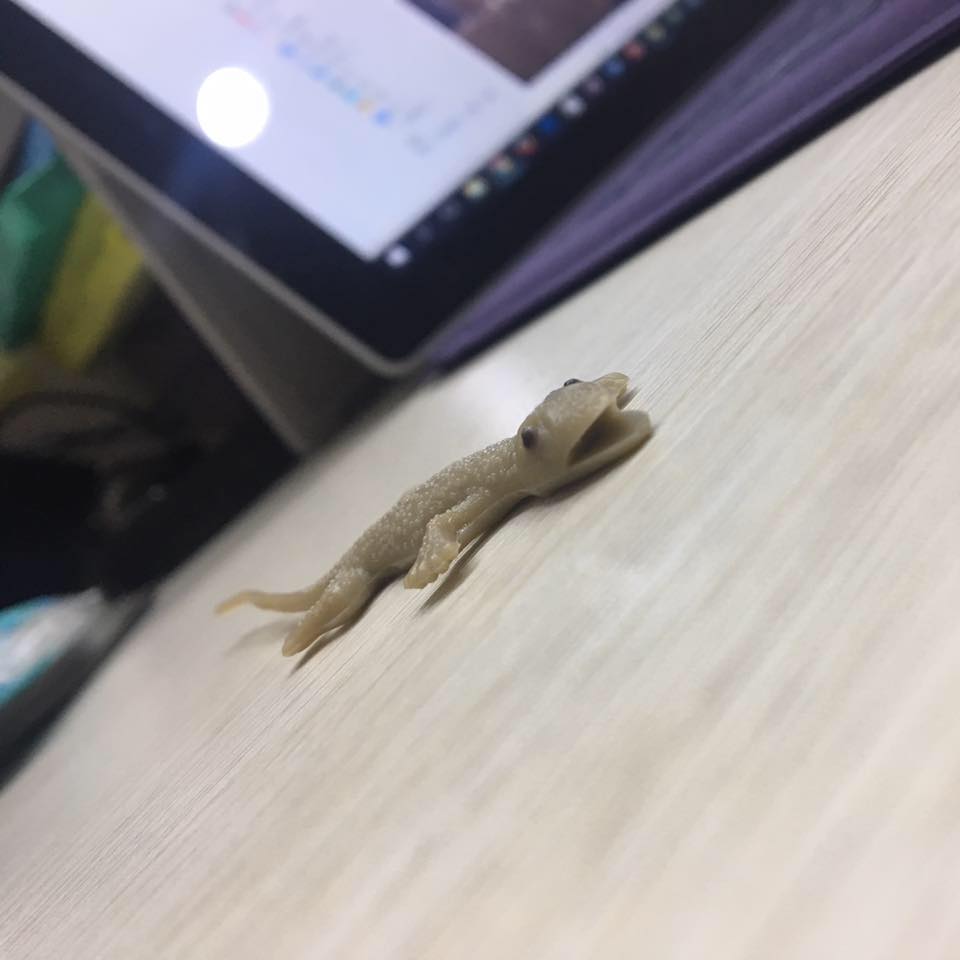|
| 《雙峰:回歸》中的諾瑪。 |
文/壁虎先生
我想雙峰鎮的鎮民最近應該都已經知道,飾演我們最心愛的RR店主諾瑪(Norma Jennings)的佩吉·利普頓(Peggy Lipton)在最近離開了我們,享年72歲。
雖然對那些25年前就生活在雙峰鎮的老朋友來說,「老去」與「死亡」幾乎就是第三季所有人的故事核心,但當諾瑪在2017年再度無預警地出現在RR的吧台前並重新以逆天的美震懾住我們的時候,我們以為諾瑪不會老去。
對利普頓我也只知道她在《雙峰》裡的樣子。在一、二季裡的雙峰鎮RR店主,賣全世界最好的咖啡跟甜甜圈跟櫻桃派,FBI探員庫柏的說法是「派如果上天堂大概就是來這裡」。永遠在罩愛上壞男孩的壞女孩、常出包的員工雪莉。年輕時也愛過壞男人,但現在只想跟老實好男人在一起,但老實好男人年輕時為了一些白癡的賭氣跟不愛的人結婚了,兩個成年人只能半夜躲在雙峰森林裡的卡車直到收音機的聲音不見。然後壞男人終於出獄了,勾勾纏云云。You get the idea. Soap opera stuff.
但如果林區有什麼座右銘,那就是他永遠不會小看通俗劇人物中的善惡。
''I'll be fine here.'',諾瑪在第二季第七集安慰雪莉,現在再看這段,能難平靜。
但如果林區有什麼座右銘,那就是他永遠不會小看通俗劇人物中的善惡。
''I'll be fine here.'',諾瑪在第二季第七集安慰雪莉,現在再看這段,能難平靜。
很難想像利普頓曾經在60年代末是多不得了的女神,事實上林區也不知道,據他的說法,他沒看過《The Mod Squad》,只是在看到利普頓的時候發現「啊這就是諾瑪!」而已。
曾經在60年代過上一段嬉皮生活,也曾經被一個叫保羅‧麥卡尼的渣男渣到,演過《The Alfred Hitchcock Hour》之類的東西,直到在1968-1972年的ABC影集《The Mod Squad》中飾演嬉皮女主而爆紅,這個講述三個惹上麻煩的嬉皮作為交換條件,必須幫警察執行臥底任務的影集,號稱是主流電視劇首次描繪嬉皮文化的嘗試。
以《The Mod Squad》的角色,利普頓拿過金球獎(提名了四次),出過專輯,單曲上過Billboard,後來跟大名鼎鼎的昆西·瓊斯(Quincy Jones)結婚,之後就漸漸淡出螢光幕過家庭生活,直到1990年和昆西·瓊斯離婚,並且在同年以另一個ABC影集《雙峰》中諾瑪的角色重出江湖。